165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整理 | 实习
在全年的四十六期编辑部聊天室中,我们试图在日常中捕捉文化的趋势,以及时下人们的心态。记得去年也在这个栏目盘点了世界上的年度关键词,包括日韩的年度词汇、《咬文嚼字》的年度词汇、《柯林斯词典》和《剑桥词典》以及《韦氏词典的》的关键词等。听了那么多别人的关键词,不知编辑部各位你们自己的年度关键词是什么?
流行文化关键词
“白女”

尹清露:我的第一个年度关键词是“白女”。这期《承认吧,我们都有过憧憬“成为白女”的时刻 》的流量和受关注度都很高,我们不仅回忆了小时候看过的小妞电影或是小时候对于白女风潮的印象,还有很多理论性的探讨。
回看这期聊天室,有几个观点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同时它们也不断地被现实印证着。例如子人认为白女之所以成为流行,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来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其实是在鼓励我们模仿白人,特别是模仿欧美发达国家的白人”。同时她也提出质问,“当东亚女性憧憬‘成为白女’,我们是否在逃避身处性别、种族和阶级交叉性下的多重弱势处境?”
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于是我观察到,今年3月初我们还在聊被标签化的“白女风潮”以及一系列单品反映的审美风格,到了下半年大家已经很少谈论这股流行,反而多了很多“韩女风潮”的帖子,比如化妆风格要学韩女,要画出很粉嫩、很温柔的妆,还有传说中的韩女三件套:眼线笔,眼影,睫毛膏。时髦的变化速度很快,这是否也体现了我们自我认同心态的变化?
最近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们单飞后集体闯进欧美音乐圈,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嘲讽跟质疑。比如Jennie(金珍妮)新歌的第一句就是“Just touched down in LA”,还有直接出了一整张专辑的Rosé(朴彩英),新专辑曲风也是完全没有K-POP的痕迹,完全是想要混进主流欧美音乐圈的状态,昨天我还刷到消息说Lisa要出演《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她饰演一位泰国女服务员。我看到中国观众对她们的评价有一些嘲讽,比如“原来K-POP偶像最终的道路也是闯美”“闯美也并不是很成功”“音乐质量并不高,尤其是跟欧美主流音乐相比”等,作为同样身处东亚的观众看着另一个东亚国家闯美,然后提出质疑,这件事还挺值得玩味的。

东亚和欧美在心态上的不同也在这个话题中被体现出来了。例如Rosé在出这张独专的时候被人评价“唱腔有点腻”,因为在以前的K-POP歌曲中,她只需要唱她自己的部分,在属于她的那一两句中表现得足够亮眼就可以了,但一旦她用这种唱法重复地将一首歌从头唱到尾,就会让人觉得有点腻。我觉得这是不同娱乐生态下培养人才出现的一种残忍的差别,可能对于欧美的女歌手来说,她们可以更自如、更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跟音乐的灵感,一开始就不需要进入韩娱的体系里面进行程序化的训练,包括她们本身进入主流国际音乐系统也很顺畅,所以我们面对欧美的时候依旧有着挫败感和这种追随的感觉。
“再见爱人”
潘文捷:我的年度关键词是“再见爱人”。最近它的收视率呈现断崖式下跌,分水岭就在李行亮和麦琳和好并相拥而睡之后,我觉得这个现象还蛮有意思的。节目一开始我是站李行亮的,过了一阵子我又站麦琳,然后我就在想:大家那么喜欢讨论自己在为谁站队,为什么就在他俩和好之后收视率完全下跌了?在各种各样的广告加入节目之后,反而已经没有人看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有一点像生活当中闺蜜跟你吐槽她的男朋友,让你给他们调节家庭矛盾,当你义愤填膺一顿分析之后,结果转过头来他俩就和好了,只剩下你一个人尴尬地在留在原地。
一开始喜欢讨论这件事,是因为很想分析这些人物的底层逻辑,比如杨子和留几手,他们多多少少能展现出来各自的人物逻辑,让人知道他们想要和不想要的是什么。反观麦琳和李行亮,他们什么都不说,反而会让观众觉得他们只呈现了30%的自己,下面还有70%是需要猜的,所以大家很愿意去猜,猜的同时又可能把两人想得很坏。

之前我们分析过短剧火爆的原因,要想让一部短剧变得更有意思,就要不断地加剧冲突,赢得观众的共鸣和渴望,在每一集结束的时候扔出“钩子”,让观众忍不住期待下面的剧情。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再见爱人》收视的暴跌,你会发现麦琳的之前许多做法就是在不断地加剧冲突,原本只是夫妻两人间的矛盾,麦琳会把这个冲突加剧到所有人的行程上,这时就会给观众带来强冲突的刺激,会让大家不自主地想看下去。然而这两人的结局却在节目播出的中途就给了观众,不论是支持李行亮或是麦琳,大家好像都不满意这个结局,尽管他们两个人可能满意了,但大家也失去了兴趣。
“精神状态”/“治愈”
徐鲁青:我的第一个年度关键词是“精神状态”/“治愈”。今年常常听到大家用各种话语描述自己的精神状态,比如“精神状态很美”之类的词,包括钝感力、淡学这些也属于“精神状态很美”的一部分,大家好像都在发疯搞抽象和精神状态很美之间摇摆,所以我觉得这可以成为年度关键词之一。我聊完《精神卫生中心文创大卖,是“精神状态美丽”的一种结果?》那一期后发现,大家对于精神状况有自己的体认,还会将其当作自嘲的单品。
在这个关键词下的还有《毛绒玩具、爽文和K-healing:到底什么是“治愈系”?》,提到了日本治愈系的发展脉络。《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一书就提到,治愈和残酷是彼此交织的,当人们找不到工作、觉得事业和恋爱都很困难的时候,才会在偶像身上寻求治愈。比如日本偶像团体AKB48的歌很有元气,但这些艺人的现实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此外,这种偶像的选举形式是为了降本增效才产生的,公司通过这种残酷的形式扩大艺人的社会影响力,这就是治愈和痛苦彼此交织的感受。《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作者斋藤环提到,治愈系话语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大家需要确认,确认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能说明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当代年轻人求职不成的痛苦并不是害怕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这样单纯的心理,而是社会价值体系太单一了,这其实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欲求。在现在的求职系统里,找不到工作时可能会被同龄人鄙视,当自我认同受到伤害时,就会催生一系列这类自我治愈的话语。
现实主义
董子琪:我的关键词是现实主义。春节档电影那一期聊天室我们讨论了“当小人物取代大故事,电影里的现实主义是更多还是更少?”,从市场层面分析了现在春节档观众不足、市场体量不够大导致的影视制作不够多元,又从投资方和创作的角度出发,发现轻松的、小体量的喜剧电影能够获得资本的青睐,再到文化层面,文捷又讲到了传统叙事的成立是因为小故事总能指向大的信仰,而对此观众是买单的。子人的观点是,小人物电影反映的也未必是现实,而是对于观众情绪的挑动和回应,《热辣滚烫》就是如此。
刚看完于和伟主演的电视剧《我是刑警》,相比于传统虚构或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探案剧,这部电视剧几乎是1:1还原了真实案件,包括事件和案件侦破环节,例如周克华案。一方面,这样的还原能够体现警察办案的辛苦劳累和奔波,犯罪分子超乎常人想象的冷酷,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还原的执着确实影响了观看,变成了一种特别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东西,遮挡了观众的视野。例如剧中主角秦川,对领导和权威专家的不服和质疑让他崭露头角,但当他走向那个位置、成为中昌省刑警队副队长之后,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容置疑的形象,他的正确和权力已经牢牢地结合了,没有人再挑战他。这个人物退休之后要怎么办?这个局面要怎么发展?

现实主义这个词贯穿了本年度很多文化作品、影视以及讨论,我们对作品“是否远离了现实”也十分关注。现实主义是否有一种标准化的叙事,这种标准化又是否穷尽了现实的所有可能,还是它只是迎合了不容言说的答案,最终变成照本宣科?这些年的不少电影比如《八角笼中》《年会不能停》《逆行人生》,以及电视剧《凡人歌》,从大凉山的贫困儿童讲到中年失业的城市白领,都触及到了一些现实,但它们到底是在表现现实,还是在利用这个题材?这是可以区分和再讨论的。就像刚才清露说的,白女的审美是一种流行工业的主流,那是在我们国家,“现实主义”是文化表达上的主流。
社会心态关键词
“中式恐怖”
董子琪:我今年特别能够体会到“吞噬感”,人好像到了一个节点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吞噬掉,比如说你工作的目标、育儿计划、雄心壮志、专业要求。你会发现你的朋友突然被吞掉了,她已经在扮演着那个特定程序中的个人,而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这好像也是一种丧失。
联想到今年最后一个关键词——中式恐怖。当时我们从游戏风格聊到诡异的、黏腻的感受,又讲到了恐怖不在于外部怪物或者暴力,而是来自于内心。恰好我今年读到了一句博尔赫斯引用的爱伦·坡的对话,有人问他“你写了这么多恐怖故事,你是不是属于什么德国浪漫派?哪个作家影响了你?”,他的回答是:恐怖不来自德国,而来自于灵魂。
我觉得说得特别对,恐怖、压抑本来就是身处文明中的我们灵魂的战栗,我小时候就有这种体会,所以才会对那些怪物恐怖特别着迷,我想这种感受能够解答当代人的很多表现、很多冲动。
“淡学”
潘文捷:我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淡学”。编辑部聊《是退缩与麻木,还是逃避统治的艺术:“淡学”是个什么学?》这一期的时候觉得我是个淡人,想知道为什么,后来看到一篇帖子说:所有喜欢睡觉的INTP都必须查一查你的维生素D。我去医院的时候也询问了医生,医生告诉我不能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必须晒太阳,不然的话就补充一些维生素D,这样才会精力充沛。
于是我在想,原来我不是性格是这样,而是生理因素导致。后来又看了一些分析,其中说到,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你的脑内就会自动增加“不希望他人进入”的空间,进而产生社交厌恶的感觉,这是变成“淡人”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当我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特别收拾,那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很淡的,但是我如果好好地捯饬了一下,就会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那时候的状态就很“浓”。
《〇〇年代的想象力》的作者宇野常宽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件好事,这让我吓了一跳,深入了解一下,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状况叫“一人公司”,我有些朋友就是一人公司,比如他们自己创业当了翻译公司的老板,他们根本一点都不“淡”,可以说是超级“浓”,会从头到尾都表现得非常完美,社交也非常积极,一个场合里可能认识一半的人,每个人都打招呼,“浓”得令人发指。

宇野常宽 著 余梦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10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身处的环境会改变他/她的浓淡。我看到一些女性主义者一边批评服美役一边化妆贼熟练,甚至还要做点医美,还有人一边批评新自由主义,但其实这些人是完全按照如何在新自由主义下更好地生活的那一套去做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原来浓人是这样炼成的,没有人是天生的浓或者淡,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淡妆浓抹总相宜(笑)。
“钝感力”
尹清露:今年我一直在践行“钝感力”,比如说如果文章有恶评的话,我会马上劝自己忘掉,如果是好的评价,我就会让自己尽量记住,感觉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不过子琪也提到过,思维敏感的时候会带来更多的醒悟或者体悟,如果过于“钝感”甚至麻木的话可能会缺失掉一些本来可以有的体悟,麻木和钝感就是一线之差。今年虽然挺钝感的,可是好像也失去了更细微的感受力,连发微博都发得很少。
刚刚鲁青提到精神卫生,包括对事情的乐观是一体两面的,快乐背后就是绝望,我觉得钝感力也一样的。颜世安在《游世与自然生活:庄子评传》中描写的庄子也是这样的,看似游戏人间,很戏谑地看周围的一切,但其实对人世间有很深的厌弃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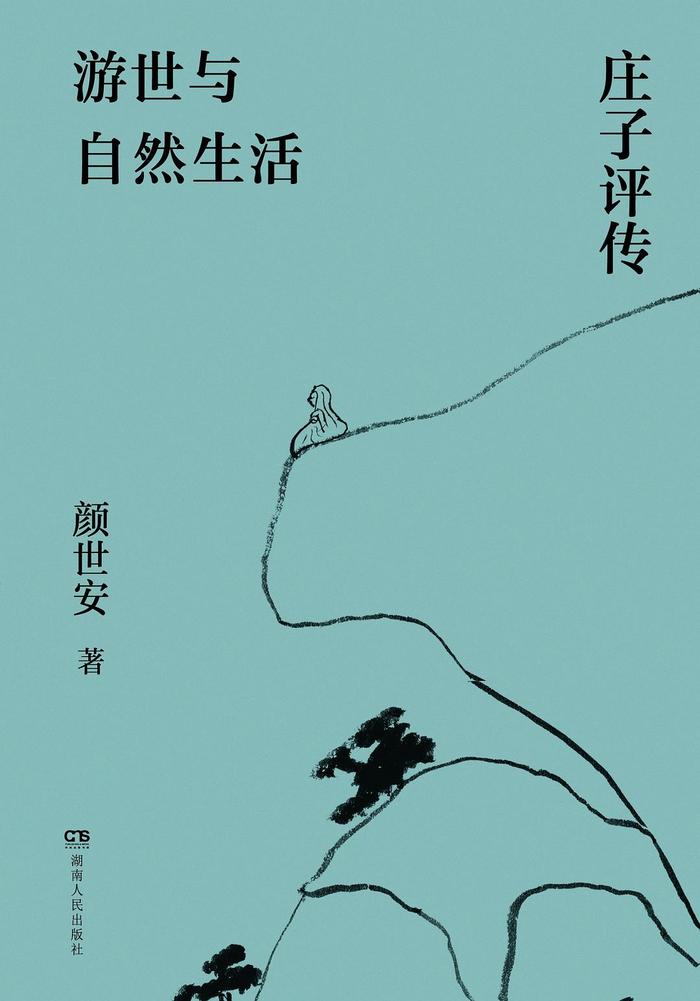
颜世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2-10
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庄子的游世思想中隐含着一个主题——带有自虐意味的嘲讽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这里的对抗不是正面反抗,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乎的姿态直视黑暗世界任何可能的恶意摆布,并且以对这种恶意摆布的戏谑的欢迎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嘲讽。这可能也是现代人的某种心态,这种自虐的感觉也跟《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有关。
“不确定性”
徐鲁青:我的另一个年度关键词是“不确定性”,那一期聊天室聊得还挺感动的,最后清露提到“以希望作为方法”的概念启发了我,就是某个部落的人做事情是以希望而不是目标为依据的。刚刚子琪说今年的聊天室我都在聊“怎么办”,这些问题背后的主线在于:想要知道我们做某个选择/决定/行动的时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那些不假思索的理念是如何构造了我们的生活。
比如在一个常规的现代社会里面,我们默认做事的流程就是先有一个目标,然后评估这个目标能不能达成再去做,而过程中的这段时间是被轻视的,最后真正有价值的时间是到达终点的时间,可是终点之后又有下一个终点,所以清露提到的《The Method of Hope》(以希望作为方法)对我的启发还挺大的,这或许就是“另一种生活”的力量,也是抵抗单向度的方式。有时候看子琪的文章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你写做梦、魂灵、死亡,虽然你不一定是从人类学的入口切入的,但是你的思考也和平时惯例逻辑、理性推理这一套思考概念很不一样。

尹清露:刚刚鲁青说因为看到另外一个体系的生活状态或者思维状态而感到安慰,我还觉得挺欣慰的。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上一次我们聊不确定性时,我表达了“可以不用追求确定”的观点,鲁青说这是一种存在主义,我回去仔细地想了一下,这其实并不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还是世界框架之下的一种个人选择,但是hope是另外一种世界观,它是以个人对抗社会框架之外的另外一种体系,意味着你的行动随时会影响到下一步的进程。
《The Method of Hope》书中就提到,对于斐济人而言,他们不是像鲁青提到的以目标为依据,通过线性时间不断达成目标,而斐济人之所以持续保有hope的感觉,是因为他们的行动跟时间本身是相关联的。有人问斐济人“你考不上学怎么办?”,当地人就说“那就再看喽”,所以他们的行动永远是会影响到接下来他们整个世界的变动的。
换言之,如果说我们一直以来深信的是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固定的世界,也许hope的世界观是:我跟世界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我的行动会自然而然地改变时间线本身,从而影响世界本身的运行。它是另外一种本体论,或者说另外一种生存观念。不是说你要去主导、掌握这个目标,掌握这个世界,也不是说你被这个目标所吞噬,不是这样一种关系。
董子琪:用hope收尾蛮好的!是个光明的结尾,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保持希望。




